2019年3月24号,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华厅举行了一场“全球经济新格局下的中美关系”的对话,美国前财政部长、总统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受邀发表了主旨演讲。
他回忆道:“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是在40年以前,我在上海主街上踱步,马路上基本没有汽车。那个时候,要给美国家里打一个电话我必须去邮局,等好几个小时,得到一个质量非常糟糕的通话。40年后,看看我们的变化是多么的巨大!”
40年前,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30年前,上海浦东还是一片农田。如今,它们都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金融或科创中心。21世纪初,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只有3%,而现在已经到了15%。这一切,都归功于4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
增长与贫困
一个略带悲剧色彩的现实是,个人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她)的家庭背景,而且,这种现象似乎还在不断地凸显。所以,类似于“寒门再难出贵子”这样的言论,总能激发越来越多人的共鸣和痛处。
但是,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个人的成就(暂且将“成就”理解为收入水平),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她)的国家背景(出生地)。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罗德里克(Dani Rodric)为了考察学生对全球不平等程度的直觉,总是在第一堂课上问他们是愿意成为穷国中的富人,还是富国中的穷人。其中,“富国”被定义为人均收入处于所有国家最靠前的5%的国家,“穷国”则是最靠后的5%的国家。相应的,“富人”和“穷人”是指在一个国家内部的财富分配中靠前和靠后的5%的人。而且,回答这个问题时,仅仅考虑消费水平,而不考虑政治和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的因素。调查的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都希望成为穷国中的富人,但实际情况是,富国中的穷人的平均收入是穷国中的富人的平均收入的5倍。
虽然这是罗德里克教授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计算的数字,但从过去近20年全球贫富分化的趋势来看,穷国与富国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如图1),而且,如果再考虑财产性收入,这种差距将会更加显著。
图1:全球收入不平等的状况仍在不断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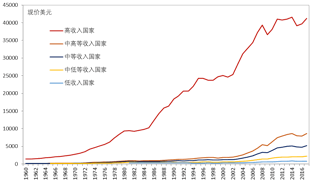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东方证券
所以,个人的经济财富,首先取决于他(她)的出生地,其次才是他(她)在国家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位置。全球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在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而非国家内部,而且,这种不平等状况还在不断加剧,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罗德里克教授想借此说明,全球化并没有消除不平等,而是在加剧不平等。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故事中看出,经济增长对于消除贫困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我们都是见证人,因为都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亲历者。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385元人民币,40年后的2018年为64644元。40年间,增长了167倍。与此同时,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也从1978年的7.7亿,降到2018年的3000万,世界银行统计的每日消费1.9美元(2011年购买力平价)以下的贫困人口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66.2%降为0.7%。
经济增长对于消除贫困的意义是首要的,也是各国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道德意义。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Ravallion & Chen,1997;Dollar & Kraay,2000),一般而言,总体经济的增长比财富的重新分配更能使穷人脱贫。这一点,已经是经济学的共识。
增长与分配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均贫富的结果是共同贫困。4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开了与贫困国家的差距,但与此同时,中国内部的贫富分化也越来越严重。
以国家统计局的数值为例,从衡量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来看,中国1978年的数值为0.18,2018年的数值为0.47,期间的最高值为0.49,出现在2008年和2009年。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计算的2010年的数值为0.61。如果考虑财产性收入的基尼系数,分配不均的状况会更加严峻。
中国的分配不均,具体体现在城乡分配不均和东中西区域分配不均。分配的不平衡,是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到的“不平衡”的主要内容,也因此被认为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在“不平衡”之前,先要解决“不充分”问题,而不充分,则与增长密切相关。因为,“没有经验证据表明,在中等收入阶段,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情况下,收入分配状况可以得到改善。相反的情形是,在经济增长及收入增长停滞的条件下,收入差距往往进一步恶化”(蔡昉,2014)。经济增长,本身就是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条件。解决不平衡的问题,还要从解决不充分着手。增长是第一性的,分配是第二性的,颠倒了次序,就会加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
那么,如何把增长与分配结合起来?就笔者的理解,这并不是一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中国当前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思路,就是从供给侧入手,同时缓解需求侧和分配侧的矛盾,这可以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政策中得到体现。
具体而言,供给侧挑战的一个体现是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由此导致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发挥作用,而与此同时,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却难以填补缺口,这必然表现为潜在GDP增速不断下行。如图2所示,中国在2004年出现刘易斯拐点(蔡昉,2014),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从无限变为短缺。这一年,广东出现了“民工荒”,至今已经成为常态。普通劳动者工资开始快速上涨,经济增长从刘易斯的二元发展模式,转变为新古典增长模式。紧接着,在2010年,以15-64岁人口为代表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行,人口抚养比开始上行,人口红利渐行渐远。
图2:中国潜在GDP与实际GDP增速的变化(1979-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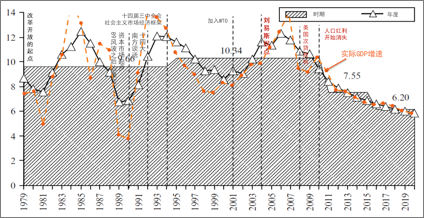
资料来源:陆旸和蔡昉(2013),WIND,笔者绘制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是需求侧冲击,却开启了中国GDP增速趋势下行的“周期”,因此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下行,本质上还是需求侧的,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所以,政策的目标是重新把需求找回来,比如用人民币贬值的方法来刺激出口,或者用扩张信贷的方法来刺激资本形成等等。过去10年的信贷和影子银行的膨胀,以及海量货币的创造,与GDP增速不断下行趋势的对比,已经证明,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出在需求侧,而只是表现在需求侧。所以,要解决需求侧的问题,还需从供给侧下功夫。
如何理解这背后的逻辑?
如前所述,分配不均是制约需求的重要因素,但导致这种不均衡状况的,却是制度壁垒所导致的供给不足。
从劳动力供给来说,周天勇和王元地(2018)认为,在诸多造成GDP下行的体制性障碍中,人口流动受阻所带来的累积效应,是这次经济增速放缓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Whalley和Shuming Zhang(2004)模拟分析的结论认为,如果取消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劳动力迁移的制度性障碍,现存的收入不平等状将会全部消失。蔡昉(2011)也认可户籍制度改革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性。除此之外,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约束,与户籍制度的挂钩所造成的公共服务分配不均等一系列制度壁垒,都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而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收入差距的贡献率高达40%-60%(万广华,2007)。这些制度壁垒增加了农民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成本,降低了农民从农村退出的收益,结果就是,农村滞留了近7000万“错过城市化”、未来也将不太可能再被“城市化”的人口;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阶段不匹配;城市劳动力的短缺;以及制造业全球竞争力的下降。
所以,新时代中国改革的先行举措,一定是从新制度着手,逐步消除劳动力自由迁移和定居的障碍。就在笔者写作当日(4月8日),国家发改委下发文件,积极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 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 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 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基于上面的分析,可知此举措对于缓解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分配不均的状况,都有显著的正面意义。
增长与失业
凯恩斯之前,没有宏观经济学,也没有经济学家关注失业问题,因为在古典经济学范畴,任何失业都是暂时的,完全弹性的工资会使得失业率永远呈现出向自然失业率收敛的态势。但是,1929年-1933年的大萧条所造成的长期失业现象,使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经济周期与失业。
最先建立起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经验关系的,是1968年被任命为约翰逊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阿瑟•奥肯(Arthur Okun,1928-1980),这个经验关系被称为“奥肯定律”,坊间将其简化为“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呈现反比例关系”,但这种简化,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严格来讲,“奥肯定律”中的经济增长,是相对于潜在增长率而言的,所以指的是产出缺口,而失业率,也是相对于自然失业率而言的,即就业缺口,代表的是周期性失业的大小。所以,原始的“奥肯定律”的意思是,实际GDP增速低于潜在GDP 2%,失业率便高于自然失业率 1%,产出缺口与就业缺口的比例为2:1。当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比值会有所差异,但反比例关系已经被大量经验证据证实。
基于简化的理解,每当失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时,用刺激需求的政策促进GDP增长,总被视为“万灵药”。那么,为何美国的经济增速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失业率却与中国相当,真是有时还比中国低?为何中国GDP增速在不断下行,失业率却没有出现明显上行的趋势?
这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是与其潜在增速下行相一致的。从图2也可以看出,2016年-2019年,中国GDP潜在增速为6.2%,这与实际情况,与政策目标也是一致的。所以,只要GDP增速与潜在增速保持一致,从而产出缺口为0,就不会存在周期性失业问题。相反,如果用需求政策刺激GDP,使其超过潜在增速,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过度繁荣,实际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出现本应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未成年人提前进入职场的现象,透支的将是未来人力资本的积累,损失的是长期GDP增长。
结语
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开创性作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提出了什么决定了一国财富多寡的问题。故纽约大学教授威廉•伊斯利特(2016)说:“自从有了经济学家这个职业,寻求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论就一直困扰着我们。”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88)也说:“(经济学家)一旦开始考虑经济增长,便无暇他顾。”这足以说明,探寻经济增长的奥秘是经济学家这个职业存在的“合法性”的来源。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本质上是供给侧占主导,而通过需求侧表现出来。解决方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供给侧改革的优先事项,是那些兼具分配侧和需求侧含义的“新制度”供给。
2018年,中国人均GDP为9630美元,离世界银行划定的12736美元的高等收入标准相差近3000美元。从当前的趋势来看,在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中国或将在2022年前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余下的不到五年闯关期,政策上不应该再以需求侧政策为主导。这是因为,供给侧决定的潜在增速才是中国能否长期维持在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终极答案。
用萨伊的话来说就是:“仅仅鼓励消费并无益于商业,因为困难不在于刺激消费的欲望,而在于供给消费的手段,我们已经看到,只有生产能供给这些手段。所以,鼓励生产是贤明的政策,鼓励消费是拙劣的政策。”
(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