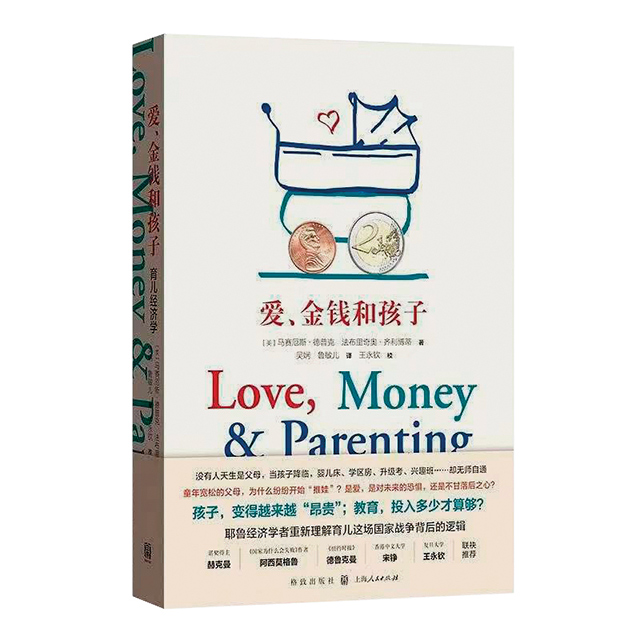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
(美)马赛厄斯·德普克等著
吴娴译
格致出版社
2019年6月
焦虑似乎已经成了新的“中国特色”,而最让中国家长焦虑和纠结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孩子的教育。
育儿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特别令人焦虑的社会话题或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缺乏一个一贯的理性视角有关。许多家长整天焦虑,但是真的认真思考过“育儿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要怎样育儿才是合理的”等问题吗?这时候,我们需要经济学思维。
美国耶鲁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两位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两人合著的《爱、金钱和教育:育儿经济学》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育儿问题的框架。两位经济学家秉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开创的思路,揭示了家庭育儿决策背后的经济机制和经济规律。特别可贵的是,这本书视野非常开阔,讨论同时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令人信服地阐明了经济激励和约束如何影响了不同国家的育儿习俗。
中国家长焦虑的根源
《育儿经济学》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从美国到中国,无论富裕抑或贫穷,不管男孩还是女孩,世界各地的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快乐成长,有所成就。然而,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却千差万别。美国和中国的父母越来越权威、专断,“育儿战争”日益激烈;而北欧的父母相比之下更为宽容。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接受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的假设,父母总是爱自己孩子的,愿意在教育孩子上进行投资。更具体地说,对于孩子,父母一方面是利他主义的,愿意付出高昂成本——时间、精力、金钱、面子等——去提高孩子的福利;另一方面,父母又是父爱主义的,认为应该为了孩子未来过得更好,适当限制孩子当下的快乐。父母同时存在利他主义和父爱主义动机,不同的父母之间的区别只是两种动机的强烈程度不同。在此基础上,父母实际做出的育儿投资决策,则取决于不同环境下的经济激励和约束,而且环境是会改变的。
德普克和齐利博蒂在考察了北欧、美国和英国、日本和韩国以及中国等国家的育儿方式随时代演变的过程后指出,经济不平等状态是决定不同育儿方式的关键因素:收入差距越大,父母在育儿上的投入就越大,父母就越可能采取密集型的育儿方式,尤其是当收入不平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教育回报率上升的时候——教育回报率越高,收入越不平等,父母在育儿上的投入也会越大。
这个答案不可能有错。但是对于中国家长来说,本书提出这个问题和给出答案的方式可能会有点误导。众所周知,父母和孩子之间最常见的分歧,就在于如何权衡当下快乐与未来成功。如果孩子当下的快乐,能够有助于他们未来的成功,那么中国家长肯定就不用这么焦虑了。
这里首先要破解一个误区。北欧各国的宽松育儿方式,绝不是对孩子的不管不问。(符合上述假设的)北欧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可以说也是密集的,只不过这种“密集性”主要体现在投入的时间和感情上,而不像中国家长这样主要体现为要代替孩子做出许多决定、要花费掉大量金钱让孩子学这学那。
中国家长很清楚,育儿要付出代价,他们也非常愿意付出。这不是他们焦虑的原因。他们焦虑的原因在于,明明知道在这种育儿方式下,孩子现在不快乐,而且这种当下的不快乐不一定有助于孩子未来的成功,但还是不得不继续这样做。
从经典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角度来说,教育也好,健康也好,花掉的支出既是消费也是投资。如果今天的投资,不能成为消费(一般来说,消费应该能够给孩子带来快乐),反而只能成为一种耗费,甚至可能还会对未来的资本产生反面作用,被迫进行这种投资的家长怎么会不觉得焦虑呢?更何况,还有很多中国家长在进行育儿投资时根本就没有明确目标。
北欧父母当然也在育儿上进行投资,只是他们投资效率更高,投资目标更明确;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育儿投资,“天然”避开了前述父母与子女的核心冲突。而北欧家长的幸福(以及北欧孩子的幸福)很大程度上也就体现在这里:孩子成长过程中所能享受到的快乐,对他们日后的成功是有利的。
这从《育儿经济学》一书引用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结果也看得很清楚。在北欧各国,人们认为想象力和独立性是孩子需要学习的最重要的态度或价值观。北欧父母希望孩子日后成为这样的人,他们所处的环境又有利于他们尽力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这样的人,孩子自己也可以快乐地成为这样的人。真是太幸福了!但是真的能够一直如此吗?未必。事实上,北欧育儿方式向美国方式趋同的变化已经在发生。
育儿投资为何陷入困境
常言道,魔鬼在细节中。《育儿经济学》一书最精彩的地方,我认为就是两位作者对各国大学管理制度和大学入学制度的细节比较分析,这是育儿决策的直接约束条件。某个国家可选的、水平差不多且都很高的大学数量比较多,而且“高考”的分数不是唯一或最主要的决定入学的因素,那么父母在育儿上的投资就可以比较灵活(如北欧和德国)。相反,如果一个国家顶尖大学数量很少,而且“高考”的分数是唯一或最主要的决定入学的因素,那么父母可以选择的育儿投资就非常有限了——事实上,只能投入激烈的育儿战争。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情况大致如此。
但是德普克和齐利博蒂对中国的分析仍然有些流于表面化。中国的大学管理制度和大学入学制度的问题,除了顶尖大学数量过于有限、入学几乎完全依赖高考分数之外,更重要的可能是高等教育供给管制和户籍决定论式的入学机会不平等。
将中国的情况与美国的情况做个粗略的比较,也许有助于说明这一点。美国的大学分层也非常严重,学生为进入顶尖大学而展开的竞争也非常残酷。但是与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那些为了进入最好的大学而参加残酷竞争的美国学生(及其家长)是主动选择的,在为进入大学而准备的过程中习得的能力,对日后继续学习有用。相比之下,中国学生(及其家长)则是被裹胁的,他们用来获取高分的能力,基本上只有敲门砖的作用。这是供给管制导致需求方选择权受限的一个典型例子,而入学机会的户籍不平等,则使之雪上加霜。
中国家长“言必称清华”,说明育儿投资决策已经陷入了困境。从根本上说,许多中国家长的育儿投资并没有明确目标,他们并不清楚希望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也无暇考虑自己的孩子希望自己未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当然,这不能全怪家长;事实上,即便是“希望孩子将来可以赚更多的钱”这样一个笼统的目标,家长们也无法有效地坚持(孩子未来的收入水平,是衡量育儿投资是否成功的一个比较没有争议的指标)。
他们在实际进行育儿投资时,只能落实为“上一所好的幼儿园”“上一所好的小学”“上一所好的中学”“上一所好的大学”这种目标,而实现这些目标的条件,则是足够好的分数。这样一来,育儿往往最终归结为让孩子取得更好的分数,尽管他们知道,中小学阶段的分数远远不等于未来获得较好收入的能力。因此,即使育儿投资实现了阶段性目标,也可能不利于长期目标。至于那些未能取得阶段性成功的家庭所白白耗费掉的资源,就更加不用提了。在这个意义上,严格地说,中国家长在育儿上的许多投入,甚至根本不能构成投资。
《育儿经济学》的作者声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介入,以纠正市场失灵。但是,中国和美国,在育儿方式越来越密集这个现象上,症状似乎是趋同的,原因其实并不一样。中国教育最紧的约束是供给管制,板子不能过快打到市场失灵上。从根本上说,任何市场,只有在真正扩大了之后,才对弱者最有利。教育也不例外。培育一大批好大学(但不必一定是规模很大的大学),应是当务之急;向私人开放大学教育市场,应该是最能起釜底抽薪之效的方法。
家长能够做些什么
人在个体层面上没有能力直接改变社会环境,因此一般而论,面对经济日益不平等和教育投资回报率增大的趋势,作为中国家长,参与育儿战争是一个理性选择。而且,这也不能去怪“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任何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都会受到社会环境和政治经济体系的影响,说中国家长就是喜欢“鸡娃”,然后从道德上加以谴责,实质上会起到为真正的制度问题开脱的作用。
在《育儿经济学》中,德普克和齐利博蒂告诉我们,一定要有动态的思维,今天的工作岗位,也许明天就不见了。因此,除了培养健全的人格之外,开发和保护孩子的兴趣和天赋将变得非常重要。
在这方面,一定不要落入空洞的“减负”陷阱,那其实只是限制作为需求方的家长的选择权的一种形式;相反,或许应该让孩子在早期的时候尽可能多上兴趣班(而且不可限于学科兴趣班)。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多上兴趣班可以说是一种风险投资,作用是有助于发现孩子的天赋,保护孩子的兴趣。万一孩子真有天赋,那么就有机会摆脱成为考试机器的路径;即便孩子没有天赋,也可以拥有更丰满的人生,不会在考完试就陷入空虚。
(作者为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