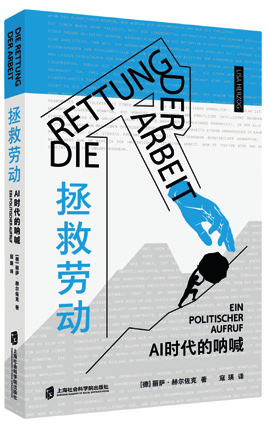
《拯救劳动——AI时代的呐喊》
[德]丽萨·赫尔佐克 著
寇瑛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5年4月
不久前,笔者参加了欧洲一家著名商学院组织的活动。活动场面相当豪华,有新鲜的水果、丰盛的小吃和一本厚厚的、为每位参与者准备的、人造革封皮的笔记本。当打开它时,笔者不仅发现有常规填写自己姓名和地址的空行——这样笔记本一旦丢失就可以寄回给失主,而且下面还有一行字:“作为答谢,您将获得____美元的酬谢。”
与其他参加活动的哲学学者一道,笔者思考了这个奇怪的想法,那就是人们为了找回笔记本到底会填写多少数额。笔者并不反对失主给拾得者酬金的原则,但在这里,这一想法似乎是在暗示人们仔细考虑,这个数额达到多少他们才会寄回拾到的笔记本。当然,那些在这类商学院中参加进修项目的“高管”们,在这一空白栏中会填上比大部分其他人更高的数额。
这一趣事中的讽刺意味在于:我们这些哲学学者受该商学院的邀请参加一个试验项目,即与经理人讨论道德及其在商业世界中的实施。因为即使在商学院这样一个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经济教学圣地,人们已经认识到,近几十年来所经历的那种没有约束的资本主义破坏了环境、割裂了社会,甚至也没有让那些看起来是赢家的人感到开心。该项目的所有参与者都意识到,经济体系不能简单地再这样继续下去了,而是亟须改变。然而,整个环境仍然表达出这个以利润为导向、以地位为象征的世界的旧有逻辑。包括笔记本的制造商都认为,如果没有精确的酬谢金额,人们绝不会愿意将笔记本归还给失主。
我们在商学院进行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现阶段的情况:从理论上讲,几乎没有人仍然主张片面追求利润;要求加强市场约束的呼声逐年响亮。但经济世界的实践,尤其是对高层人士的培训,直至最细枝末节之处都仍然表达着“芝加哥学派”、哈佛商学院、像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迈克尔·波特这样的经济学家向世界传达的信息:人是自利的,这是一件好事,利润导向最终将服务于社会;“贪婪”是正确的,拼命竞争是正确的。
从历史性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发生在我们早已意识到经济的人类形象——
仅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经济人的片面性之时;而与此同时,这一人类形象仍然深深地根植于经济世界的结构和实践之中。因为有强大的利益集团坚持维护没有约束的资本主义制度。数字技术引发的变革导致原本可能隐藏于表面之下的冲突暴露出来。这些冲突不仅是不同群体之间的,而且也是不同价值观之间的。过去经过艰苦谈判达成的妥协破裂了;试图在不同价值观之间找到平衡点的努力常常不得不重新开始。最好的情况是,民主公众及其政治机构可以通过谈判达成与新技术现实相称的新妥协方案;最坏的情况是,最有权势的群体以牺牲整个社会为代价,无所顾忌地实施意图。
这种冲突也围绕着如下问题展开,即以何种人类形象引导即将进行的改革,因为不同的人类形象隐含着对什么构成了美好生活以及谁有权享受美好生活这一问题的不同答案。在一本装订精美的笔记本上,预设归还酬金的空白栏隐含着几十年来世界各地经济学院和商学院所教授的人类形象:人们按照经济激励行事,他们不是情绪化的,而是冷静算计自己的行为,所有的事情都必须(且可以)用美元来衡量。
因此,目标是确定使人们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的确切金额。这种观念并非完全错误,但它忽视了人类动机、人类需求和人类共存的许多方面。被忽视的清单很长,这里只提几个关键点:人们通常想要自己做正确的事情;他们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十分不同的行动;有些事情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也许最重要的是,人是社会人,他们关心他人的福祉,特别是他们朋友和家人的福祉,并且寻求他人的认可。作为社会人,我们共同塑造我们的世界,而不只是自私地追求个人利益。
在塑造数字化转型的政治斗争中,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哪种人类形象能够引导数字化转型,当然还有哪些群体以何种方式从中受益?答案涉及社会的许多领域,比如社交媒体和“数字公共领域”、健康数据的使用或提升职场竞争力的教育和培训类平台等。
然而,最激烈的争论可能是关于劳动世界的构建问题。我们会面临完全依赖机器及其所有者而进行无意义劳动的至暗场景吗?还是我们能够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的劳动世界,因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或许可以为子孙后代提供更好的生活?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化转型是按照“经济人”的老调子进行,还是成功地塑造了符合人类社会本性的数字化转型。
劳动、团结、民主平等
人们为什么想劳动?他们最关心的似乎往往是收入。但除此之外,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往往还缺乏一些东西:社会交往,走出有时相当狭窄的家庭和邻里圈子,遇到有着不同世界观和背景的人。当然,人们也可以通过参加俱乐部、教会团体或政党与人交往。
然而,只要还存在这样一个雇佣劳动的世界,它就有潜力成为一个社会融合的场所,此外还给人们带来可靠的日常节奏,并通过社会期望产生约束。这并非偶然,我们社会中的许多边缘化人群,无论是难民还是无家可归者,他们最想要的就是一份工作:不仅是为了赚取自己的收入,也是为了成为在劳动世界中形成的社会网络的一部分。
埃米尔·杜尔凯姆为社会凝聚力的不同形式创造了两个概念。前现代社会所谓的“机械”团结是基于相似性原则:在这里,人们与他人的共同特征才有效,个人特征无法得到发展;而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则以差异性为基础:人们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杜尔凯姆根据这两种社会凝聚力形式各自伴随的法律形式,讨论了这两种形式的发展。在“机械”团结中,“约束性法律”的作用是惩罚偏离共同准则的违法行为,而“有机”团结主要需要一种“恢复性法律”,来调节劳动分工产生的合作关系。
每个社会都需要某种团结形式,作为社会凝聚力的基础,即使在一个越来越多的劳动由机器人和计算机程序支持甚至接管的社会亦是如此。劳动分工越是明确的社会就越需要,因为分工劳动的结构中存在许多破坏的机会。对于杜尔凯姆来说,回归“机械”团结并不值得向往,因为个体的个性可以在“有机”团结的现代社会中得到比在前现代社会中更好的发展,后者压制一切偏离准则的行为。“有机”团结是与现代劳动分工一起形成的,但只有在满足某些条件时。杜尔凯姆谈及,一定的“为生活而斗争的外部条件的平等”是必要的,以便各个个体的不同“功能”可以有意义地相互连接起来;否则,“契约团结”就会丧失,即遵守契约的意愿会丧失,那样就只能依靠“暴力或对暴力的恐惧”才能得以保证了。
杜尔凯姆就社会团结和社会公正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为了让人们认为交换是公平的,其必须以“同等的社会价值”进行。但不能“先验地”(a priori),即从实际交换关系中抽象出来,确定所交换商品或服务的价值。当行为者可以在没有强迫和不平等权力的情况下建立交换关系时,“等值”就出现了。但这是以个人的某种平等为前提的,否则“交换的道德条件”就会被扭曲。
所以,杜尔凯姆得出结论:“最先进社会的任务就是……实现公正。”如果出现了不公正,进而产生了不平等的权力和依赖关系,那么越来越多的交换关系将会被视为不公平的。这一思路继续发展下去,一个劳动分工但不公正的社会最终会破坏其赖以生存的基础:所有人都愿意参与劳动分工、遵守契约,并且不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来利用机会进行投机行为。
数字化社会也必须扪心自问:是否允许它完全分裂成不同的阶层,无论是在劳动世界或在其他生活领域,还是存在一些人们可以在其中保持自身差异性,但又能以社会平等成员身份相处的领域?劳动世界可以是这样一个地方吗?还是它首先是一个充满强制性和等级制度的地方?
当然,如果总体上社会不平等现象在加剧,这也势必会对劳动世界造成影响。人们可以就什么程度的不平等是合理的争论很久;但德国目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十分严重,大部分民众,也包括较高收入者在内都已对此形成共识。关于征收遗产税、修改所得税制度以及改善低收入家庭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建议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为了对一个起到社会一体化作用而非分裂作用的劳动世界产生进一步的间接影响,人们也迫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
(本文摘自《拯救劳动——AI时代的呐喊》 ;编辑:许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