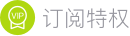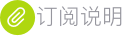1998年,经济学家樊纲在《读书》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不道德”的经济学》,激起很多的讨论。“不道德”三个字打了引号,是说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不过,文章的论点非常清晰,认为经济学不应该讲道德,它是去道德化的。其实在韦伯时代,关于经济学的价值中立也是讨论这个问题,在韦伯那里,这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只讨论怎么控制住假设,然后更好地研究一个事物的“逻辑的”因果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讲,韦伯的价值中立和我们讲的“不道德”并不是可以等同起来的一个概念。樊纲讲的“不道德”具有非常强的“科学化”经济学的意图,试图将经济学中的一切道德因素去除。他发表该文之后不久,我曾作出回应,表示了不同意见。
不过,“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没有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看起来那么容易处理,它特别有张力,一方面它承接着一个极为丰富,但长期被误读甚至完全被忽视的思想史传统;而另一方面,又与日新月异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相衔接,受到来自社会实验技术和脑科学相关研究的冲击。
从思想史的方面,我们今天可以举出的重要人物和作品非常之多,其中,最重要的一脉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哈奇逊、休谟、亚当·斯密。在近代经济学的学科化进程当中,亚当·斯密既是一个受益者,也是一个受害者。所谓受益者是因为他的《国富论》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名声,并由此成为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学之父”,西方经济学界给他的评价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斯密也是一个被后人误读最深的学者。在很长时间里,社会科学史基本上忘记了他其实是一个根本就没有学科概念总体性的思想家。后人记住了他的伟大作品《国富论》,忘记了他的另外一部更加重要的作品《道德情操论》,他被定义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位研究如何使国家致富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