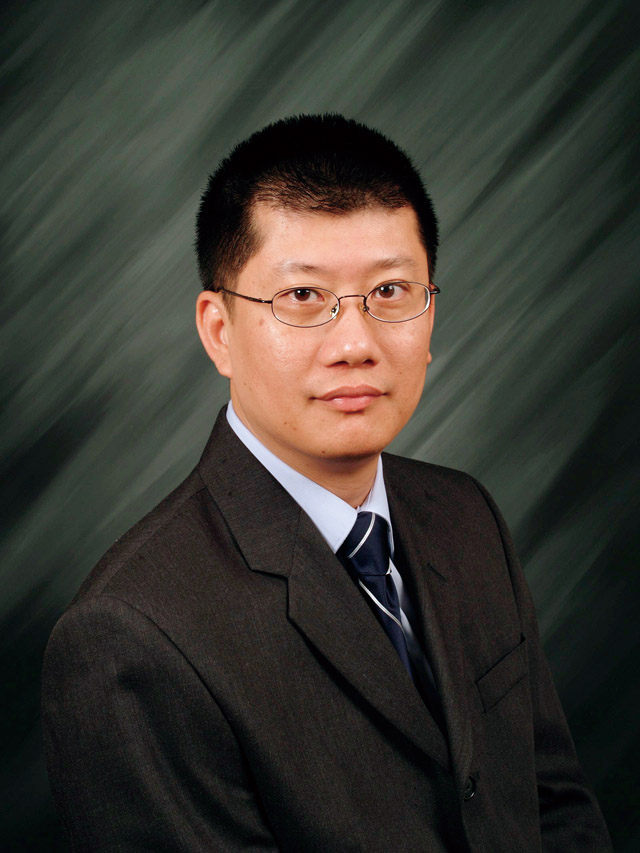
人类始终面临的约束之一是资源稀缺。所谓资源稀缺,不仅指矿产、森林和能源等有形资产的匮乏,而且还指空气、美貌、天资、时间和注意力等无形资产的不足。要高效利用资源,人们不得不作选择,而只要有选择,就必然有歧视。换言之,选择和歧视,指同一件事,是两个共生共栖的概念。
有选择就有歧视。选择一张王菲的唱片,就歧视了所有男歌星和绝大部分女歌星,也歧视了中国京剧和西洋歌剧。一个男人娶一个女人为妻,他就歧视了所有男人以及绝大部分女人。即使这个男人希望不带歧视地对待每个女人,法律也不容许。
有人反驳:“你是在偷换概念。歧视指的是那些‘不道德’和‘不必要’的区别对待。”是的,人们脑海里有许多根深蒂固的“区别对待”的观念,如看不惯外地人或外国人,或把全体异性作为取笑的对象等。
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一、由于信息不对称,要了解具体一个人并不容易,人们便简单以对群体的笼统印象代入,只求作粗略的判断;二、贬低他人可改善自我感觉,人们难免会追求廉价的快感。
问题是,歧视者必须付出代价!一个活在山沟里的人,本来就没有机会与外人打交道,所以他不妨把外人贬得一钱不值。本来就没有机会,歧视就没有代价。然而,一旦他有机会进城,或有机会出国,那他歧视外人的代价——因歧视而丧失的收益——就会急剧提高。输得越多,放下成见的动力就越大。多见少怪,长此以往,都市居民的胸襟往往比较开阔。
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组织内部。在私营企业里,雇主关注金钱收入,所以在录用员工时,会集中考核其劳动力资本,而对其他旁枝末节,诸如肤色、户籍、党派、政见、相貌、学历等并不关心。相反,在大型国企或政府机关,选人是否得当,几乎不影响录用者的收入,所以录用者就会变得轻视“有用之人”,转而偏爱“顺眼之人”。
人们普遍的经验是,越是激烈竞争的行业,歧视越少;越是大锅饭的垄断或官僚机构,歧视越严重。
这是说,歧视与选择共生,但随着迁徙、交流、贸易和竞争,“不道德”和“不必要”的歧视自然会受到抑制和削弱。既然如此,那么政府颁布法令或发起政治运动,是否也有助于纠正“不道德”和“不必要”的歧视?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自上世纪60年代起,美国掀起了“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联邦和州政府纷纷颁布“平权法案”,禁止基于“肤色、宗教、性别或民族出身”的歧视。然而,这项运动的实质,恰恰是越俎代庖地为用人机构作了基于“肤色、宗教、性别或民族出身”的反向选择。
1973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根据“平权法案”,为非白人硬性预留16%学位,致使成绩更好的白人青年贝奇(Allan Bakke)不被录取。要知道,非要让成绩较差的黑人学生就读学医,今天受到歧视的就是白人学生和亚裔学生,明天受到损害的就是病人。要帮黑人是对的,但不是这样帮。
此事到1978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加州大学的做法违宪而告一段落,加州也在1996年推出了还学校更大招生自由的法律(CCRI),从而部分纠正了“平权法案”造成的矫枉过正的恶果。
然而,许多人还没有完全理解问题的本质:选择是一种重要的自由,而选择与歧视不可分;用一刀切的“平权运动”来纠正种种“歧视”,并不能消灭不公,只能转移不公;只有还个人和用人机构以充分的选择权,并让迁徙、交流、交易和市场竞争发挥作用,从而促使人们逐渐采用更合理的选择标准,才是维护“自由”(liberty)的正道。
作者为经济学者、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