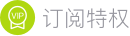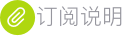在很多场合,我们本能地知道,如果以当下的“我”的感知作为基点来向别人传递信息会是无效的。例如,当你迷路了给警察打电话,警察问你在哪里,你不会说,我就在我在的这里啊。你总是得找一个独立于你的客观的锚来让别人对你进行定位,否则,没有人能够知道你感知、意识到的那个“我”是怎样的、在哪里等。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我们也都知道,客观化的事实陈述(或命题)具有这样的形式:“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某事”,它是“去个人化的”,也就是说,不是以“当下的我”的感知为锚来讲话,而是以人际间的某种客观的存在作为参考基准来讲话。
不管是哪种情况——是陈述关于个体的事实也好,还是关于外部事件的事实也罢——主体间能够有效传递的,都只能是基于独立于个体感受、感知的客观的“锚”得以陈述的事实,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自动地就会发现,当你迷路时,对方没办法“锚定”你到底在哪里,当你在表述一件事情,其他人不懂你到底在说什么。
维特根斯坦说,构成世界的,不是事物,而是事实;他还说,一个命题的含义就是它被核实的方法。我上面讲的,也可以算是对这两句话的诠释。